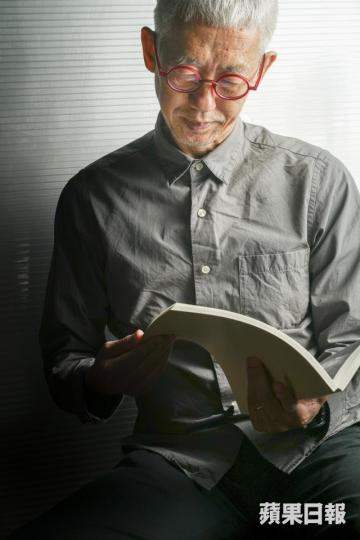新聞類別
副刊
詳情#
【蘋果日報】在剛過去的藝術中心攝影書展,有一本新書名為《Secret香港樞密1842-1997》,以白色文件套包上,文件套封口有一條幼繩連起兩個小圓扣,一紅一藍,代表「中、英兩國的糾纏」。封套內承載的是九七前港英政府跟中國政府的多份往來文書,年代最久遠的上溯至清廷割讓香港的1842年。攝影師黃勤帶在英國檔案館拍下百多份解封的檔案,輯錄成書,以影像訴說歷史。
以檔案為攝影題材,而非單純記錄實體文件,手法甚是冷門。原來打字機油墨字和墨水筆手寫字,以大特寫方式呈現,會滲出獨特美感;玲瓏剔透的朱紅火漆印,飽滿多姿。書中包含極珍貴的歷史痕迹,包括戴卓爾夫人及趙紫陽簽署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,和麥理浩、習仲勛(習近平之父)的餐桌名單。
撰文、攝影:何少忠(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)
黃勤帶這名字在香港紀實攝影界數一數二,曾出版《89廣場上的日子》、《填海記》、《北京戀曲》及《皇后旅館》等攝影集,題材圍繞北京,以及殖民地時期的澳門和香港,黑白對比非常強烈,不像一般新聞圖片。《香港樞密》的拍攝風格,卻跟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。
拍攝工作始於2000年。當時黃勤帶的太太在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寫博士論文,題目是香港回歸與傳媒轉變,需要到國家檔案館(The National Archives)搜集相關檔案參考。「由於影印檔案的收費昂貴,我做了『影帝』,替她拍下數以千計的照片。」他自嘲,一生人影最多照片的工作就是那一次。
黃勤帶的攝影風格獨特,唯獨在倫敦替太太翻拍資料時,卻不能有任何自己的風格,每張相都要影得清清楚楚,把文件內容拍得纖毫畢現。
翻拍的過程中,黃勤帶被這些檔案的歷史內容和質感打動,後來決心用自己的角度再記錄一次。2006年與太太重回倫敦,他把一部小型數碼相機架在檔案館提供的專業翻拍台上,利用窗外的天然光照亮歷史文件,陽光偶爾令歷史的質感立體起來,雖然晴朗的天氣在倫敦還是罕有的。
根據港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解釋,英國的檔案法規定,公務人員在公事活動過程中,必須開立檔案。官員做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個決定,均須立案為證。公務完成後,檔案須送交政府的檔案管理機構鑑定,有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國家檔案館永久保存。若非敏感資料,檔案封存20至30年後便會開放予公眾人士查閱。
力透紙背的歷史感
全書最重要的,要算是1984年簽署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副本,這份決定幾百萬香港人命運的協議上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、中國總理趙紫陽的簽名。兩國元首的簽署外,還有象徵兩國承諾的朱紅火漆印,上有中英兩國的徽號。香港百多年的殖民命運,就在那一刻改寫。
黃勤帶這本攝影集,輯錄了114張照片,像這一頁聯合聲明,將內容完全呈現眼前的其實不多,很多圖片他都只選取文件的一小部份,例如一份文件提及一部中方直升機入侵香港領空,他只特寫了文件的左上角,最重要的內容像事件的年份都裁切掉。
「我並非為了那些詳細內容,那是研究歷史的人的工作。我純從視覺角度記錄文件的質感、歷史的痕迹。」
纏着舊香港地圖的布繩、顯示粗幼紋理的紙張、玲瓏浮凸的皇室蓋印……這些都是黃勤帶鏡頭下的質感和痕迹,滲透在全書之中。
「清政府用毛筆寫的『照會』,有港英政府的印章,是香港百多年殖民地歷史,中英糾纏的象徵。」他激動地說。
黃勤帶過往的作品個人色彩濃厚,很多時只有意會,不能言傳。「用文字說明我的照片,不是我的習慣。我過往的書都沒有任何圖片說明,我的意圖是用純影像紀錄歷史,不像報紙裏的新聞圖片。」
在以往的出版如《皇后旅館》,首任特首董建華喪父時披麻戴孝跪在靈堂送喪的照片;港督尤德訪京、衛奕信出巡的照片,都不附上任何文字說明。但他明白這次若不用文字說明圖片,會為讀者帶來不便。本書在最後頁附上每張圖片的簡單索引,已是他最大的妥協。
舊檔案中穿越時空
一幅幅富歷史感的圖片,像藝術品一樣呈現,不用受文字說明「滋擾」,但他明白一般香港人未必都能接受。說到這裏他頓了頓,從記者手上輕輕取回相集,搜尋了半晌後展示一張簡單的晚宴主家席的座位圖,圓形飯桌旁有各人的名字。
「我這本書也有八卦的元素。這是港督麥理浩宴請嘉賓時的座位表,坐在他旁邊的是當時廣東省省長習仲勛先生,即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。席上還有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等。」這樣一張平平無奇的簡陋座位表,竟也能保存下來,英國人尊重歷史,可見一斑。
他又翻開另一頁「八卦嘢」。「在倫敦大學修讀中文的港督尤德,曾在文件的邊緣寫上幾個中文字:『借主人的酒』。」這個主人意指尤德訪京時的主人家北京政府。尤德被稱為中國通,就香港前途問題多次在北京發表演說。兩國「官話」蘊含巨大文化差異,這一頁文件裏,他與同事斟酌“borrowing your wine”在中文實際含意為何,並寫上中文字作補充。
在倫敦翻拍文件的過程中,黃勤帶無數次跟太太進出位於郊外列治文區(Richmond)的國家檔案館。每次進入都要經過安檢,離開時亦不能帶走館內任何東西。閱覽室內有閉路電視,檔案館亦提供手套讓訪客戴上,確保所有人適當處理檔案。訪客想看的檔案,職員會用盒子載着或舊白布包裹,珍而重之如文物一樣遞上。但始終文件老舊,他見過有人閱後歸還檔案,桌面卻留下一整塊剝落的舊書脊。
查閱檔案的人來自世界各地。「印度人查閱遙遠的殖民地檔案,遠道而來的美國遊客,查閱先祖在英國的歷史。在蜂巢形的工作桌,大家都沉默穿梭於不同的時空。」
為歷史留紀錄
黃勤帶上世紀70年代末加入《文匯報》當攝影記者,後來在報館鼓勵下到日本進修攝影三年,回港後繼續在《文匯報》當攝記至1989年六四後不久離開。因緣際會,他在北京見證了八九民運。
「89年4月原在北京拍攝一宗體育新聞,台灣體操隊首次到北京比賽,碰巧同月胡耀邦逝世,引來前所未有的人群聚集北京悼念。」他跟報館拿了大假,繼續記錄北京民運的影像,回港後出版過三本六四相集。今年六四30周年,他曾經考慮重新編訂舊相集內容,並加入未曾曝光的圖片,再度出版,但最後擱下大計。
「我原想用較大的尺寸重編六四的照片出版,可惜大尺寸攝影書要給內地印刷廠,由於這是敏感題目,我便打消了念頭。」
正值香港出現訂立檔案法的討論,政府更承認曾經銷毀相等於不知多少幢IFC高度的檔案,引起公眾譁然。黃勤帶從櫃桶底尋回兩張記憶卡,裏面記錄了無數攝於2006年英國檔案館的圖片,他決定把圖片編印成書。
「為何會出這本書?因為香港社會變得好快,正面臨一個舊記憶消失的境地。我們要跟鄰近地區融合,將會創造一個新的歷史記憶,舊記憶將會消失。
「香港有150年深層歷史,我們不是深圳,那是一個複製香港的城市,打做出來的地區,外形上可複製,但無法製造自己的歷史。我們有自己的歷史,便應好好保存。」
「香港不是第三世界,連一個檔案法都拋來拋去傾唔掂,任何一個官都可消滅檔案,英國人卻連一頓飯的座位表都留下來。我們有哪個公務員有資格判斷一份文件的價值?你又不是歷史、檔案專家。」
「這些檔案等如香港人的身份證,一個成熟社會要有自己的記憶。歷史就是歷史,好的壞的,屈辱也是歷史,都要尊重。香港的出現,殖民的出現,當中管治如何,留下了甚麼紀錄,這全是一個地方的身世。我為一些檔案造一個紙本紀錄,算是盡了本份。」
長青網 -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
以檔案為攝影題材,而非單純記錄實體文件,手法甚是冷門。原來打字機油墨字和墨水筆手寫字,以大特寫方式呈現,會滲出獨特美感;玲瓏剔透的朱紅火漆印,飽滿多姿。書中包含極珍貴的歷史痕迹,包括戴卓爾夫人及趙紫陽簽署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,和麥理浩、習仲勛(習近平之父)的餐桌名單。
撰文、攝影:何少忠(部份圖片由被訪者提供)
黃勤帶這名字在香港紀實攝影界數一數二,曾出版《89廣場上的日子》、《填海記》、《北京戀曲》及《皇后旅館》等攝影集,題材圍繞北京,以及殖民地時期的澳門和香港,黑白對比非常強烈,不像一般新聞圖片。《香港樞密》的拍攝風格,卻跟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。
拍攝工作始於2000年。當時黃勤帶的太太在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寫博士論文,題目是香港回歸與傳媒轉變,需要到國家檔案館(The National Archives)搜集相關檔案參考。「由於影印檔案的收費昂貴,我做了『影帝』,替她拍下數以千計的照片。」他自嘲,一生人影最多照片的工作就是那一次。
黃勤帶的攝影風格獨特,唯獨在倫敦替太太翻拍資料時,卻不能有任何自己的風格,每張相都要影得清清楚楚,把文件內容拍得纖毫畢現。
翻拍的過程中,黃勤帶被這些檔案的歷史內容和質感打動,後來決心用自己的角度再記錄一次。2006年與太太重回倫敦,他把一部小型數碼相機架在檔案館提供的專業翻拍台上,利用窗外的天然光照亮歷史文件,陽光偶爾令歷史的質感立體起來,雖然晴朗的天氣在倫敦還是罕有的。
根據港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解釋,英國的檔案法規定,公務人員在公事活動過程中,必須開立檔案。官員做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個決定,均須立案為證。公務完成後,檔案須送交政府的檔案管理機構鑑定,有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國家檔案館永久保存。若非敏感資料,檔案封存20至30年後便會開放予公眾人士查閱。
力透紙背的歷史感
全書最重要的,要算是1984年簽署的《中英聯合聲明》副本,這份決定幾百萬香港人命運的協議上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、中國總理趙紫陽的簽名。兩國元首的簽署外,還有象徵兩國承諾的朱紅火漆印,上有中英兩國的徽號。香港百多年的殖民命運,就在那一刻改寫。
黃勤帶這本攝影集,輯錄了114張照片,像這一頁聯合聲明,將內容完全呈現眼前的其實不多,很多圖片他都只選取文件的一小部份,例如一份文件提及一部中方直升機入侵香港領空,他只特寫了文件的左上角,最重要的內容像事件的年份都裁切掉。
「我並非為了那些詳細內容,那是研究歷史的人的工作。我純從視覺角度記錄文件的質感、歷史的痕迹。」
纏着舊香港地圖的布繩、顯示粗幼紋理的紙張、玲瓏浮凸的皇室蓋印……這些都是黃勤帶鏡頭下的質感和痕迹,滲透在全書之中。
「清政府用毛筆寫的『照會』,有港英政府的印章,是香港百多年殖民地歷史,中英糾纏的象徵。」他激動地說。
黃勤帶過往的作品個人色彩濃厚,很多時只有意會,不能言傳。「用文字說明我的照片,不是我的習慣。我過往的書都沒有任何圖片說明,我的意圖是用純影像紀錄歷史,不像報紙裏的新聞圖片。」
在以往的出版如《皇后旅館》,首任特首董建華喪父時披麻戴孝跪在靈堂送喪的照片;港督尤德訪京、衛奕信出巡的照片,都不附上任何文字說明。但他明白這次若不用文字說明圖片,會為讀者帶來不便。本書在最後頁附上每張圖片的簡單索引,已是他最大的妥協。
舊檔案中穿越時空
一幅幅富歷史感的圖片,像藝術品一樣呈現,不用受文字說明「滋擾」,但他明白一般香港人未必都能接受。說到這裏他頓了頓,從記者手上輕輕取回相集,搜尋了半晌後展示一張簡單的晚宴主家席的座位圖,圓形飯桌旁有各人的名字。
「我這本書也有八卦的元素。這是港督麥理浩宴請嘉賓時的座位表,坐在他旁邊的是當時廣東省省長習仲勛先生,即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。席上還有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等。」這樣一張平平無奇的簡陋座位表,竟也能保存下來,英國人尊重歷史,可見一斑。
他又翻開另一頁「八卦嘢」。「在倫敦大學修讀中文的港督尤德,曾在文件的邊緣寫上幾個中文字:『借主人的酒』。」這個主人意指尤德訪京時的主人家北京政府。尤德被稱為中國通,就香港前途問題多次在北京發表演說。兩國「官話」蘊含巨大文化差異,這一頁文件裏,他與同事斟酌“borrowing your wine”在中文實際含意為何,並寫上中文字作補充。
在倫敦翻拍文件的過程中,黃勤帶無數次跟太太進出位於郊外列治文區(Richmond)的國家檔案館。每次進入都要經過安檢,離開時亦不能帶走館內任何東西。閱覽室內有閉路電視,檔案館亦提供手套讓訪客戴上,確保所有人適當處理檔案。訪客想看的檔案,職員會用盒子載着或舊白布包裹,珍而重之如文物一樣遞上。但始終文件老舊,他見過有人閱後歸還檔案,桌面卻留下一整塊剝落的舊書脊。
查閱檔案的人來自世界各地。「印度人查閱遙遠的殖民地檔案,遠道而來的美國遊客,查閱先祖在英國的歷史。在蜂巢形的工作桌,大家都沉默穿梭於不同的時空。」
為歷史留紀錄
黃勤帶上世紀70年代末加入《文匯報》當攝影記者,後來在報館鼓勵下到日本進修攝影三年,回港後繼續在《文匯報》當攝記至1989年六四後不久離開。因緣際會,他在北京見證了八九民運。
「89年4月原在北京拍攝一宗體育新聞,台灣體操隊首次到北京比賽,碰巧同月胡耀邦逝世,引來前所未有的人群聚集北京悼念。」他跟報館拿了大假,繼續記錄北京民運的影像,回港後出版過三本六四相集。今年六四30周年,他曾經考慮重新編訂舊相集內容,並加入未曾曝光的圖片,再度出版,但最後擱下大計。
「我原想用較大的尺寸重編六四的照片出版,可惜大尺寸攝影書要給內地印刷廠,由於這是敏感題目,我便打消了念頭。」
正值香港出現訂立檔案法的討論,政府更承認曾經銷毀相等於不知多少幢IFC高度的檔案,引起公眾譁然。黃勤帶從櫃桶底尋回兩張記憶卡,裏面記錄了無數攝於2006年英國檔案館的圖片,他決定把圖片編印成書。
「為何會出這本書?因為香港社會變得好快,正面臨一個舊記憶消失的境地。我們要跟鄰近地區融合,將會創造一個新的歷史記憶,舊記憶將會消失。
「香港有150年深層歷史,我們不是深圳,那是一個複製香港的城市,打做出來的地區,外形上可複製,但無法製造自己的歷史。我們有自己的歷史,便應好好保存。」
「香港不是第三世界,連一個檔案法都拋來拋去傾唔掂,任何一個官都可消滅檔案,英國人卻連一頓飯的座位表都留下來。我們有哪個公務員有資格判斷一份文件的價值?你又不是歷史、檔案專家。」
「這些檔案等如香港人的身份證,一個成熟社會要有自己的記憶。歷史就是歷史,好的壞的,屈辱也是歷史,都要尊重。香港的出現,殖民的出現,當中管治如何,留下了甚麼紀錄,這全是一個地方的身世。我為一些檔案造一個紙本紀錄,算是盡了本份。」
長青網 -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
回應 (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