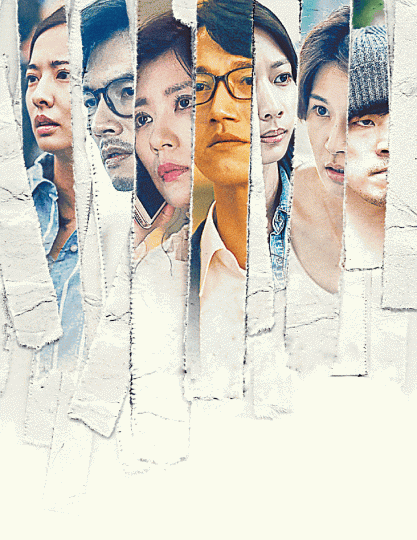新聞類別
港聞
詳情#
【蘋果日報】「這是台劇新本土運動的高峯。」台灣資深影評人鄭秉泓說。台劇一片低迷,在這片迷霧中,台灣公視劇集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(下稱《與惡》)竄起,收視率集集叫好,在豆瓣、IMDb都獲9分以上推薦。在大結局播出前,還收到對岸「青睞」,先流出簡體高清影片。到底是甚麼讓人着急探討起我們與惡的距離來?
記者:周凱瑩 李俊杰
法治有權力剝奪人命嗎?壞人就該被判死嗎?引劇內一句對白:「到底甚麼是好人,甚麼是壞人,你有標準答案嗎?」「廢死爭議」在台灣社會吵了20多年,依舊沒有爭論出結果。2014年北捷隨機殺人犯鄭捷,其父母也曾聲淚俱下,向民眾下跪道歉,2016年,槍聲響起,鄭捷伏法。可是犯人以死抵命就可以伸張正義嗎?
透過大數據 編出「沒盲點」劇本
「這一類片以往都沒有人敢拍。」曾擔任金鐘獎、金馬獎評審的台灣資深影評人鄭秉泓說。鄭介紹,《與惡》的編劇呂蒔媛通過大量訪問,以及利用大數據中網民就關鍵詞的對話,用多個立場,編寫出一個幾乎「沒有盲點」的劇本──從死刑犯、律師夫婦、殺人犯家屬、精神病患家屬、媒體人兼受害者家屬之間的對話,也為台灣本土多年來的爭議,提供討論的空間。恰巧,劇集也剛好碰上一個對的時間點。
「台灣今年、去年有很多假新聞、假消息,去年還害死一個外交官,讓他自殺,所以大家對假新聞,這一年來非常關注,然後剛好有一部戲,它在討論媒體亂象這件事情,又從媒體亂象講起無差別殺人事件,從很多面相去探討台灣當代社會的眾生相。」鄭秉泓說。鄭更盛讚,它是一場新本土運動,「《與惡》不商業化,呈現台灣現實感,劇本有不同年紀、不同社會階層的人,包括初出茅廬的李大芝,職場女強人宋喬安,從這些人中,構成了一個大網絡」,這也替台灣民眾的目光,暫別動輒拍上200集的8點檔、「作夢的偶像劇。」
與荷李活HBO合作 台劇走向世界
《與惡》也讓台劇面向世界的窗口。劇集除了在電視,也會在網上串流平台播放,「Local是公視播,Catchplay是播給新加坡等亞洲的、HBO是播給世界的。」鄭秉泓指,跟HBO、Netflix等國際平台合作,與這似乎是近年來台灣影視的出口。《與惡》正洽商在HBO的北美版、歐洲版播出,可視為是台劇走出國際的一大步。那會成功嗎?「(《與惡》)裏頭說的,有親情、有愛情、有無差別殺人,這些都是很universal(普世的)的。」
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莊佳穎也認為,用台灣本土案例,來包裝一些普世價值,是《與惡》成功的要素。「無差別殺人的這些犯人,他們其實心理狀態沒有被接住,那是一個全球的現象。」此外,台劇也在調整腳步。莊稱,台劇要打入大陸市場不易,因為只要有劇組人員發表過台獨言論,戲劇隨時會被封殺,「所以面向中國市場,不如面向全世界。」
事事跟黨走 大陸難拍出同類作品
台灣出品從以往《麻辣風暴》,到近年的《大佛普拉斯》、《血觀音》、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可見以撕裂的社會創作出來的文創討論度日漸提高,是因為受眾的水準提高了嗎?莊佳穎稱,觀眾的水準一直很高,「與其這樣說,倒不如說是因為這個商品本身喚醒了台灣社會,回歸去看自己的台灣劇。」莊也樂見討論《與惡》的人,不再局限於引用對白的法官、熱愛思考的文青,就連街坊、通俗的談話性節目都想與《與惡》沾上邊。
那麼,香港、大陸有機會出現像《與惡》這種作品嗎?「中國很難。」鄭秉泓斬釘截鐵地說:「中國應該是沒有了,就算有人敢拍也沒人敢播,最後的主旋律都會變成符合黨的意思」那麼香港呢?「我期待有,香港至少還有杜琪峯,而去年一部電影叫《翠絲》,是講跨性別人士的,比較貼近現實,可見香港還是有有心人。歐文傑、李駿碩也是香港的年輕人才。」
長青網 -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
記者:周凱瑩 李俊杰
法治有權力剝奪人命嗎?壞人就該被判死嗎?引劇內一句對白:「到底甚麼是好人,甚麼是壞人,你有標準答案嗎?」「廢死爭議」在台灣社會吵了20多年,依舊沒有爭論出結果。2014年北捷隨機殺人犯鄭捷,其父母也曾聲淚俱下,向民眾下跪道歉,2016年,槍聲響起,鄭捷伏法。可是犯人以死抵命就可以伸張正義嗎?
透過大數據 編出「沒盲點」劇本
「這一類片以往都沒有人敢拍。」曾擔任金鐘獎、金馬獎評審的台灣資深影評人鄭秉泓說。鄭介紹,《與惡》的編劇呂蒔媛通過大量訪問,以及利用大數據中網民就關鍵詞的對話,用多個立場,編寫出一個幾乎「沒有盲點」的劇本──從死刑犯、律師夫婦、殺人犯家屬、精神病患家屬、媒體人兼受害者家屬之間的對話,也為台灣本土多年來的爭議,提供討論的空間。恰巧,劇集也剛好碰上一個對的時間點。
「台灣今年、去年有很多假新聞、假消息,去年還害死一個外交官,讓他自殺,所以大家對假新聞,這一年來非常關注,然後剛好有一部戲,它在討論媒體亂象這件事情,又從媒體亂象講起無差別殺人事件,從很多面相去探討台灣當代社會的眾生相。」鄭秉泓說。鄭更盛讚,它是一場新本土運動,「《與惡》不商業化,呈現台灣現實感,劇本有不同年紀、不同社會階層的人,包括初出茅廬的李大芝,職場女強人宋喬安,從這些人中,構成了一個大網絡」,這也替台灣民眾的目光,暫別動輒拍上200集的8點檔、「作夢的偶像劇。」
與荷李活HBO合作 台劇走向世界
《與惡》也讓台劇面向世界的窗口。劇集除了在電視,也會在網上串流平台播放,「Local是公視播,Catchplay是播給新加坡等亞洲的、HBO是播給世界的。」鄭秉泓指,跟HBO、Netflix等國際平台合作,與這似乎是近年來台灣影視的出口。《與惡》正洽商在HBO的北美版、歐洲版播出,可視為是台劇走出國際的一大步。那會成功嗎?「(《與惡》)裏頭說的,有親情、有愛情、有無差別殺人,這些都是很universal(普世的)的。」
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莊佳穎也認為,用台灣本土案例,來包裝一些普世價值,是《與惡》成功的要素。「無差別殺人的這些犯人,他們其實心理狀態沒有被接住,那是一個全球的現象。」此外,台劇也在調整腳步。莊稱,台劇要打入大陸市場不易,因為只要有劇組人員發表過台獨言論,戲劇隨時會被封殺,「所以面向中國市場,不如面向全世界。」
事事跟黨走 大陸難拍出同類作品
台灣出品從以往《麻辣風暴》,到近年的《大佛普拉斯》、《血觀音》、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可見以撕裂的社會創作出來的文創討論度日漸提高,是因為受眾的水準提高了嗎?莊佳穎稱,觀眾的水準一直很高,「與其這樣說,倒不如說是因為這個商品本身喚醒了台灣社會,回歸去看自己的台灣劇。」莊也樂見討論《與惡》的人,不再局限於引用對白的法官、熱愛思考的文青,就連街坊、通俗的談話性節目都想與《與惡》沾上邊。
那麼,香港、大陸有機會出現像《與惡》這種作品嗎?「中國很難。」鄭秉泓斬釘截鐵地說:「中國應該是沒有了,就算有人敢拍也沒人敢播,最後的主旋律都會變成符合黨的意思」那麼香港呢?「我期待有,香港至少還有杜琪峯,而去年一部電影叫《翠絲》,是講跨性別人士的,比較貼近現實,可見香港還是有有心人。歐文傑、李駿碩也是香港的年輕人才。」
長青網 - 一站式長者及護老者生活資訊網站
回應 (0)